中共早期留苏学员的“谈话”训练
——以朱克靖相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徐霞翔
摘要: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遣四批学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受上级党组织选派,1924年6月朱克靖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除参加课程学习外,作为中国班学员中的一个小组组长,在旅莫支部的领导下,朱克靖带领组员开展“谈话”训练,注重相互批评及理论学习,强化集体意识及组织纪律观念。这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朱克靖向职业革命家转向,为归国革命做好了准备。
关键词:朱克靖;莫斯科东方大学;“每周报告表”;“谈话”
因中国革命发展需要,自1921年10月至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遣四批学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学习。[1](此为注释,具体参考文末)已有学者对中共早期留苏学员特别是东大中国班学员的“谈话”训练进行深入探析并有精到发见[2],但多侧重学员群体研究,对学员个体研究较为少见。朱克靖属第二批留苏学员序列,关于其留苏期间“谈话”训练研究,学理性的论文几乎未见,仅有几部人物传记对此稍有涉及[3],尚未构建出严谨的解释体系。本文主要根据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尝试考察朱克靖留苏期间的“谈话”情状,探析其“谈话”对象、频次、用时,着重检视其“谈话”主题及内容,由此凸显东大旅莫支部训练中共早期留苏学员之取径,并从某些侧面展现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国际化”之面相。
一、“到莫斯科去”
朱克靖原名宏夏,字竹懿,号克靖,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株树下村一个农民家庭。8岁即入本乡族学就读,14岁考入醴陵县城的中学堂,后入湖南长沙第一中学就读。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受新文化和五四爱国运动影响,朱克靖逐步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2年朱克靖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
1924年6月,朱克靖至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5]为了解留苏中国班学员各方面情况,东大校方设计出多样化的统计表要求学员填写,从中亦可见朱克靖的些许个人情况。如朱克靖的英文程度为乙等(程度分甲乙丙三等)。[6]学员《调查表》显示:在调查表的各栏目中,朱克靖“籍贯”是“湖南醴陵”,“年龄”是“二十六”(按:似有误),“社会地位”为“知识阶级”,“通何国语言”为“英文俄文”,“入党的年月”为“1922”,“加入其他团体否”为“中SY、国民党”,“附录”填写的是“北城、朱洪泰号”。[7]
初到东大的学员大都有一个俄文名字。据肖劲光回忆,他的名字是查戈洛斯基,任弼时叫布林斯基,“为的是避免将来回国做革命工作时暴露身份”。[8]朱克靖的俄文名字叫列文(Левен),此外还有“号数”是1785。[9]
东大中国班学员是由东大旅莫支部统一领导的。东大旅莫支部成立于1922年底,1926年被撤销,在其存在的4年时间里,一直是东大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留学生的管理组织。[10]为方便管理,旅莫支部将东大中国班学员分为多个小组,学员一度被分为20个小组,每组一般5人左右,设有小组长一名,如朱克靖是第19小组组长(组员有李植、糜文浩、郭玉昌、饶竞群4人)、聂荣臻是第七小组组长、李求实是第八小组组长。[11]
1924年10月,饶竞群(饶来杰)从法国至东大[12],根据安排,饶竞群被分到朱克靖所在小组,对此,半个世纪后他回忆说:
我是一九二四年十月到东方大学习(按:漏掉一“学”字),是从法国去的。朱克靖是从国内去的,比我去的早,担任我们小组的组长。我是二五年五月离开苏联回国,他是二五年下半年、二六年上半年回的国。在三军任政治部主任,他比我大一二岁,我是一九00年生的。[13]
至于在东大的学习,学员“主要是学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国际工人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及名人讲演,学习俄文”。[14]比饶竞群稍早(1923年)来东大的郑超麟回忆说,我们“课程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自然科学,俄文,似乎没有其他的科目”。[15]
在课程学习之余,东大学员必须“随时参加中共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和各项活动”,那时旅莫“支部领导人”有“罗觉、陈延年、王若飞、刘伯坚、陈乔年”。[16]郑超麟回忆说,在他来东大之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17]应该说,学员的“谈话”训练即是旅莫支部开展的“各项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活动。
二、“谈话”训练
1925年1月4日至3月28日期间,朱克靖撰写过11份“每周报告表”。朱克靖的“谈话”对象及方式较为庞杂多元,对象既有组内成员,也有组外学员;方式既有“一对一”交心,也有“一对多”交谈。而“一对多”的“多”亦有不同组合,或都为组外学员,或组内外人员混合。具体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在近三个月时间里,朱克靖与组内成员“谈话”有10人次,与组外学员“谈话”有96人次,与组内外合谈的有6人次。很明显,朱克靖与组外人员“谈话”次数远多于与组内成员的“谈话”次数,这很可能与旅莫支部要求每位党团员至少须与本组之外的“两个同志以上发生密切关系”存有关联。[18]同时不难发现,从3月份起,朱克靖对每周“谈话”着手计时,该月“谈话”共用时近30小时,每周“谈话”的平均时间达7个多小时。
从朱克靖的“谈话”主题来看,多集中于“毛病”或“批评”、“团体”或“本组”“小组”“组内”以及“训练”“研究”“国民革命”等内容[19],也从一个侧面提示出旅莫支部对东大学员的某种训练“预期”。
在1月4日朱克靖与陈乔年等人的“谈话”中,对于怎样观察和批评同志这一问题,朱克靖认为“观察是为批评,批评就要先有相当的观察,批评同志绝对不是攻击,也不是训练式的”,这就“是彼此互相批评的意义”。[20]在与稽直的一次“谈话”中,朱克靖认为“个性强就是不合于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并敏锐地发现稽直“还有两个极错误的观念:他承认自己有活动能力,但是在这环境不须他活动,如果另换一个环境,他就能积极活动起来”,这绝对是“前后相矛盾的话”。[21]
“谈话”中的相互批评似为经常性主题,朱克靖与蔡畅的一次“谈话”即展现出两人之间的“彼此稍加批评”,“她说我作(做)事不精细,我对她批评小资产阶级色彩太浓厚”。[22]对于同志的“毛病”,朱克靖认为“团体内这期同志所犯的毛病很多,但归结起来都是是(按:原文如此,应多一“是”)一个幼稚病”。[23]对于如何去除这个“幼稚病”,朱克靖提出,“对于有些同志幼稚的毛病,除训练外,尤其要多灌以无产阶级的学识”。[24]实际上,这就是要求“有些同志”实现“无产阶级化”。或许只有“真无产阶级化后,我们的革命人生观才可确定”。[25]
为促使组内成员一道进步,2月7日朱克靖的“每周报告表”中记述了他一周来与组内3位成员(稽直、饶竞群、胡越一)的谈话情况;此外,还通过组外学员王奇岳进一步了解组内成员情况:“越一个性强,自信深,对团体工作不十分积极,赵秀峰表示有进步,但城府很深,稽直太注意俄文,研究无方法。”[26]这些无疑有助于本组成员的共同成长。
在开展相互批评的同时,朱克靖时刻注意中国情况。朱克靖在与佘立亚等人的一次“谈话”中,即以“帝国主义限制中国关税的意义”为题进行讨论,得到的“结论”为,“帝国主义限制中国关税的用意在打破中国的经济独立,使中国产业破产,成为帝国主义完全的市场,并操纵中国经融机关,渐渐由经济的侵略成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27]这一点对于科学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及明确中国革命性质是相当重要的。
其时国内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朱克靖密切关注形势变化。2月14日朱克靖“与朱祺谈联合兵匪作国民革命的运动”,他认为这“是不可的,有一部份(分)兵士吾人尚可与之联合,关于土匪他并没有革命的要求,只可有相当的利用,然而还须问我们自己的实力如何?”结论是“我们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应该是工农,联合各阶级革命的份(分)子集合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28]
约一个月后,朱克靖与陈启修“谈中国国民革命将来的趋势”,认为“中国国民革命要与世界革命相联合”。[29]几天后,朱克靖“与蔡畅谈中山死后国民革命之趋势,及何如宣传的方法,大意与中央的通告相同”。[30]在此前后,朱克靖与熊雄“谈及希夷(按:叶挺)归国问题”,认为“希夷归国迟早对他本身不发生问题,全要团体视国内的情形为转移”[31]。这似乎提示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留苏学员的未来趋向。
如前所述,既然旅莫支部要求每位党团员至少须与本组之外的“两个同志以上发生密切关系”,故部分学员主动与朱克靖“谈话”也属情理之中。在1月份至3月份期间,赵秀峰与朱克靖共“谈话”4次,分别关于他“对于本期大会的批评和警告”“研究的方法”“孙继常一事”“自己当注意思疑的大毛病”。[32]2月份,稽直与朱克靖“谈话”两次,主要关于他“这两周来的概况”及“此后应注意的几点”。[33]
与上述稍有不同的是,饶竞群与朱克靖“谈话”内容多关于本组事宜,如1月24日,饶竞群“与朱克靖谈本组以后进行方针,在研究上除注意学校功课外,还应留意报纸,在活动上应多与落后同志接近,极力打破宗法社会思想并谈及他与秀峰谈话的结果”。[34]两周后,饶竞群又“与克靖谈本组进行的情形”。[35]3月份,饶竞群与朱克靖进行两次“谈话”,其中一次即他“与克靖谈稽直与秀峰最近表现的缺点及本组以后的进行”。[36]
主动与朱克靖“谈话”者,除上述组内成员外,尚有组外部分学员。如郭玉昌与朱克靖“谈西欧团体,现时有一个退出的旧团员要求复回团体的情形”,两人“又讨论”郭玉昌“对莫地团体情形”的理解,及对“关于西欧来莫廿七个同志的局部分裂情形”的认知。[37]此外,吴苓生与朱克靖“谈话”两次,内容分别为“谈引导同志的方法”及“谈我对家庭的关系,以后站在党的利益方面应当如何去解决”。[38]
根据旅莫支部要求,朱克靖或主动与部分同志“谈话”,或部分同志主动与朱克靖“谈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构建出纵横交错的革命者人际关系网络,这对于旅莫支部了解学员的思想状况,甚或促进学员之间的相互监督,都具有特定的意义。
三、结语
东大本为俄共(布)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培养职业革命家为其使命所在。而旅莫支部的“训练”方针虽与苏联创办东大的长远战略或存有一定抵牾[39],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似有“互补性”:后者较注重理论学习,前者则较注重“行动”训练。
在上述“行动”训练中,作为小组组长的朱克靖展现出鲜明的个人性格特质。据陈碧兰回忆,如果“从他(按:朱克靖)的态度谈吐以及对人处事的作风看来,他是一个异常诚实而不随声附和、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富正义感的人,他不畏权威,敢于说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意见(在全体大会上)”;特别是“当我们每次在李大钊的居室里聚餐之后,他总是抢着要洗涤餐具,甚至连我或其他同志去帮忙他都拒绝”,故“单从这一件小事来看(从小事最能看出人的品德),他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40]不过,朱克靖亦有不足之处,正如林育英提及的,他“有时热情太盛”[41],以及前述蔡畅所指责的“做事不精细”。
更为重要的是,朱克靖在东大期间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为其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42]而其中“谈话”训练则有助于朱克靖表述能力的提升及构建革命者人际关系网络,便于日后开展革命宣传动员工作。另一方面,“谈话”训练亦有利于朱克靖开展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克服“事事以个人主义出发”[43]的倾向,逐步树立集体主义观念,实现“知识阶级”的“无产阶级化”。此外,“谈话”训练也不断深化了朱克靖对中国社会情形的体认,进一步坚定对“主义”的信仰,他明言,要“在思想上,行动上,经济上,都应绝对的从宗法社会底下解放出来”,以“做一个真实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为人生目标。[44]
从朱克靖的“谈话”记述,可以管窥中共早期培养职业革命家的诸多历史细节;另一方面似乎也提示出一个隐伏的面向,即列宁式政党所具有的那种“等级结构、特殊的党员选择标准以及严格的纪律”和“能够进行快速、有效和集体行动”[45]等特质逐步浸润到中国的革命文化中,并对中国革命产生长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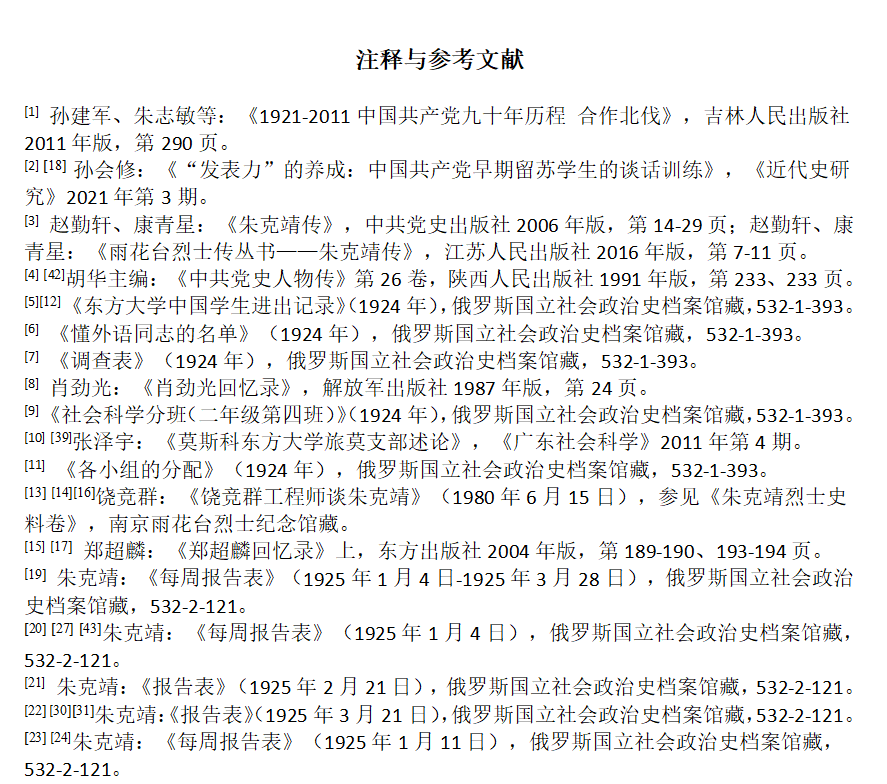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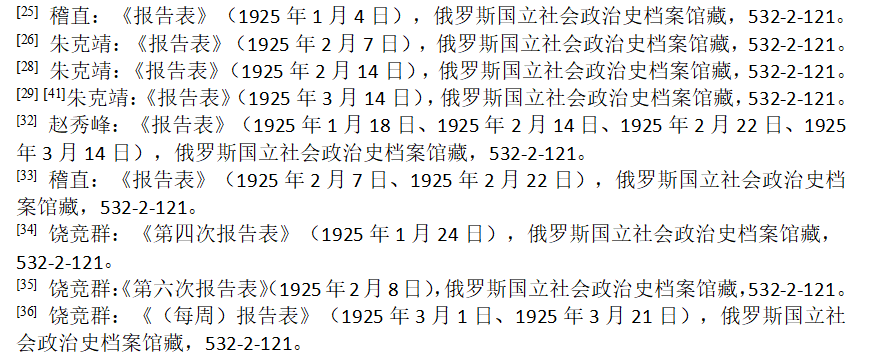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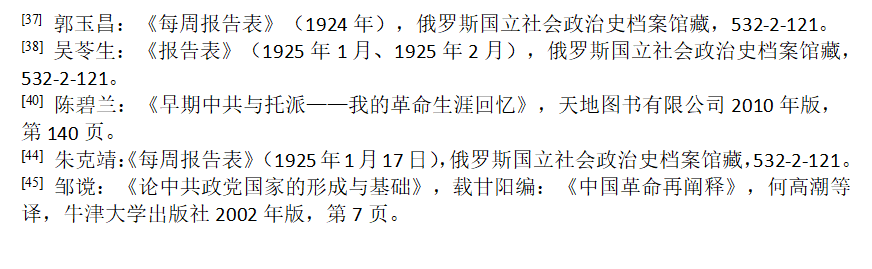

作者简介:徐霞翔,男,历史学博士,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档案与建设》2022年第11期,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精神的发掘、传承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21DJD001) ;2022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留苏雨花英烈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SYA-017)阶段性研究成果。